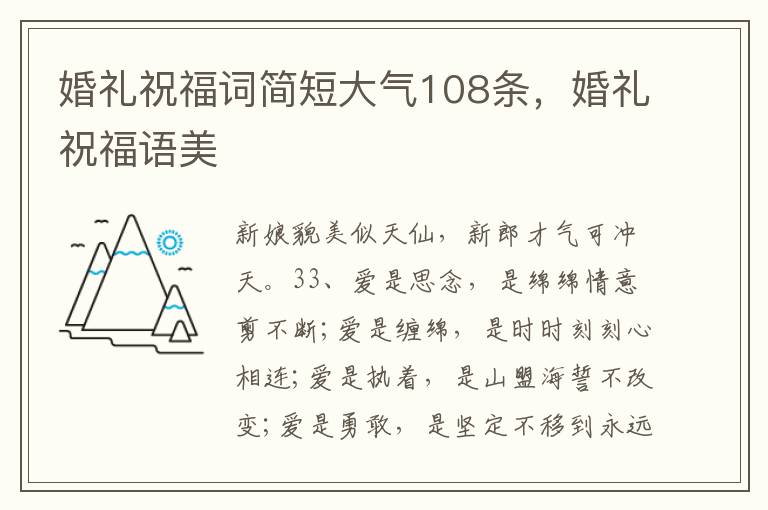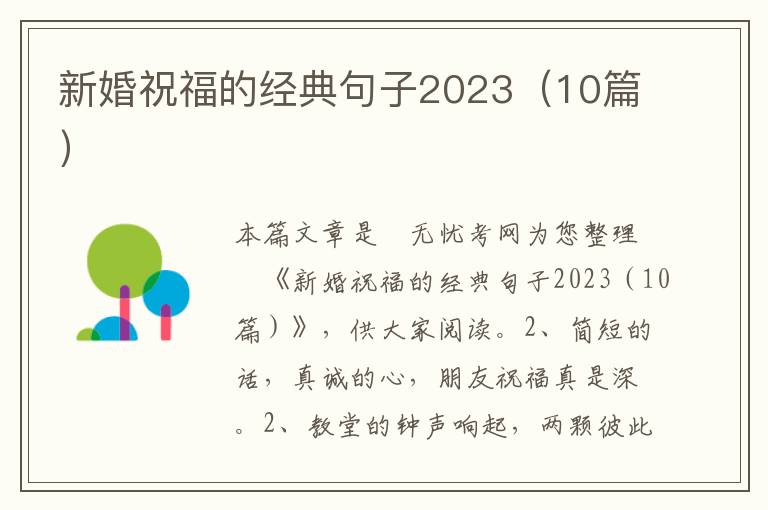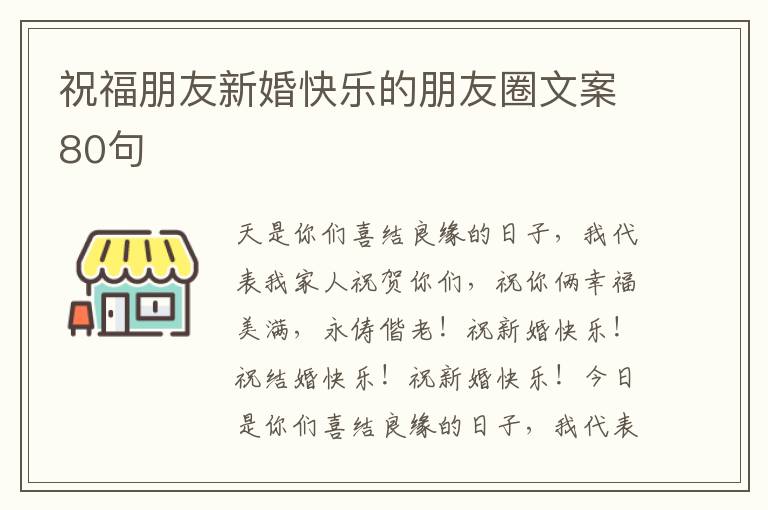普希金:我的命運已定,我要結婚

那個我愛了整整兩年的女子,那個在任何地方都被我的眼睛所首先捕捉到的女子,那個與她的相會能使我感到無上幸福的女子,――我的上帝,――她……幾乎就是我的人了。
對那一決定性回答的等待,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感覺。對最后亮出的那張牌的等待,良心上的譴責,決斗前的睡夢,――這一切和我的那一感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問題在于,我所害怕的并不僅僅是回絕。我的一個朋友常常說:“我不明白,如果你大約知道不會被回絕,那該如何去求婚是好啊?”
結婚!說起來輕松,――大部分人視婚姻為一樁欠下債務的糊涂舉動,一輛新馬車和一件粉紅色的睡衣。
其他一些人將婚姻視為嫁妝和井然有序的生活……
第三種人結婚,是因為所有的人都結婚,――是因為他們已經三十歲了。您若問他們什么是婚姻,作為回答,他們會向您說出一句下流的玩笑來。
我要結婚,這就是說,我要犧牲我的獨立,我瀟灑、放任的獨立,要犧牲我那些奢華的習慣、無目的的漫游、獨處和飄泊。
我準備將生活擴大一倍,否則這生活就是不飽滿的。我從不為幸福而操心,沒有那幸福我也能行。如今,我需要兩個人的幸福,可我在哪兒能找到這樣的幸福呢?
在我結婚之前,我都有哪些事要做呢?我有一個患病在身的叔叔,我幾乎從未去見他。我去了他那里,他很高興;不,他是這樣對我說的:“我的浪子正年輕,他顧不上我。”我沒有和任何人通信,自己的債務我在按月償還。早晨我想什么時候起床就什么時候起床,客人我想接待誰就接待誰,想到要去散散心,有人就會將我那匹名叫“熱尼”的聰明、溫順的馬備上鞍。我便騎著馬在小街上溜達,向那些低矮房屋的窗戶里望去:在這一戶,全家人都坐在茶炊旁;在那家,一個仆人正在打掃房間;另一家,一個小女孩正坐在鋼琴邊學琴,一個音樂藝人坐在她身邊。小女孩向我轉過了她那張心不在焉的臉,教師在罵她,我緩步走了過去……回到家里,我翻一翻書本、文件,把我的梳妝臺收拾整齊,隨隨便便地穿身衣服。如果要去做客,則要千方百計地精心穿戴,如果去餐館吃飯,就在那兒閱讀一本新小說,或是一些雜志;如果瓦爾特?司各特和庫珀什么東西都沒能寫出來,報紙上又沒有什么刑事案件,我就會要上幾杯加了冰塊的香檳酒,看著酒杯漸漸變涼,慢慢地呷著酒,因這頓午餐價值十七盧布,因自己可以享受這樣的奢華而感到心滿意足。我常去劇院,用目光搜尋某間包廂里的出色的打扮和黑色的眼睛;我和那人之間便開始了來往。
――直到散場前我一直在忙乎著。晚上我有時是在喧鬧的社交場合度過的,在那兒聚集著全城的人,在那兒我能見到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在那兒卻沒有一個人會注意到我。有的夜晚,我則是在親切、特定的小圈子里度過的,在這里,我談論自己,在這里,人們傾聽我。很晚方才返回:一邊讀著一本好書,一邊入睡。第二天,我又騎馬在小街上溜達,走過有小女孩彈琴的那間房子。她在鋼琴上一遍遍地復習昨天的課程。她看了我一眼,像是看見一位熟人,她笑了一下。――這便是我的獨身生活……
如果我遭到回絕,我想,我就會到國外去,――我想象自己已經在輪船上了。我身邊的人在奔忙著,告別著,在搬運箱子,在看著鐘表。輪船開動了:一陣清新的海風吹拂到我的臉上;我久久地看著愈來愈遠的岸――My native land, adieu.我身旁的一位年輕女士嘔吐起來;這使她那張蒼白的臉上現出一種受難的溫柔……她請我給她一杯水。謝天謝地,在到達喀瑯施塔得之前,我還有事可做……
就在這時,有人給我送來一張條子:這是對我的求婚信的回復。我的新娘的父親客氣地請我到他那里去……毫無疑問,我的求婚被接受了。娜堅卡,我的天使,――她是我的人啦!……在這天堂般的感覺面前,所有那些憂郁的疑慮都煙消云散了。我奔向馬車,我疾馳而去;這就是他們的家;我走進前廳;僅憑仆人們忙不迭的接待,我就知道我已經是未婚夫了。我害羞起來,因為這些人都知道我的心思;他們在用奴仆的語言談論我的愛情!……
父親和母親坐在客廳里。父親張開雙臂迎接我。他從衣袋里掏出一塊手帕,他想哭,卻又哭不出來,于是決定擤鼻涕。母親的雙眼紅紅的。他們喚娜堅卡進來;她走了進來,臉色蒼白,舉止很不自然。父親出去抱來了奇跡創造者尼古拉和喀山圣母的圣像。他們為我倆祝了福。娜堅卡把冰涼、順從的手遞給我。母親談起嫁妝,父親談起薩拉托夫的莊園,――于是,我成了未婚夫。
這樣一來,這件事也就不再是兩顆心靈中的秘密了。這今天還是一個家庭新聞,明天就會是一個廣場新聞了。
這一部在孤身獨居時、在夏夜的月光下構思出來的長詩,后來便在書店里出售,在雜志上受到一群傻瓜的批評。
所有的人都為我的幸福而高興,所有的人都來祝賀,所有的人都愛過我。每個人都提出要幫助我:有人要把房子讓給我,有人要借錢給我,有人則把與他熟悉的商人及其便宜貨介紹給了我。另有人為我未來家庭的眾多人丁而擔心,建議我與宗塔格女士的一幅肖像畫一同,買下十二打的手套。
年輕人與我在一起時開始感到拘謹了:他們敬重的是我身上非我的東西。女士們當面對我稱贊我的選擇,背地里卻在為我的未婚妻感到惋惜:“可憐的姑娘!她多年輕、多純潔啊,可他卻那樣輕浮,那樣的不道德……”
我承認,這一切開始使我感到厭煩。我喜歡古代民間的一個習俗:未婚夫秘密地把自己的新娘偷走,第二天,他便能依靠城里愛散布流言的女人們,使那位姑娘成為自己的妻子。而我們,為了家庭的幸福,卻要依靠那些傷感的表白、全城皆知的禮物、固定格式的書信、拜訪等等,一句話,要依靠各種各樣的招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