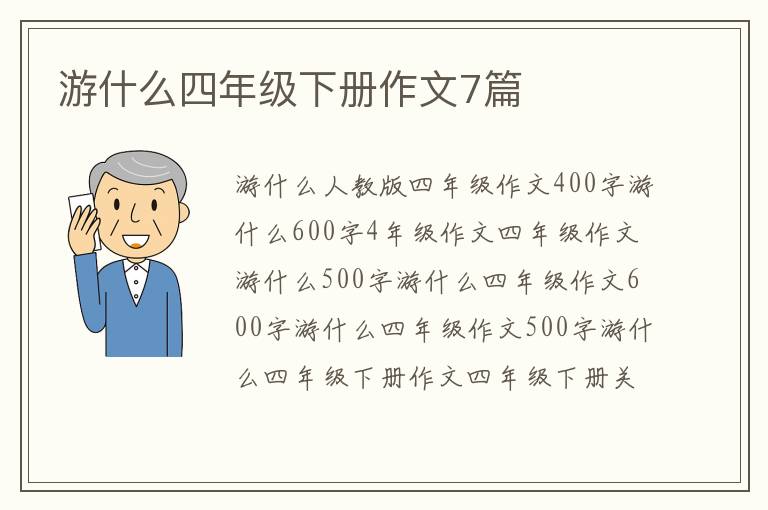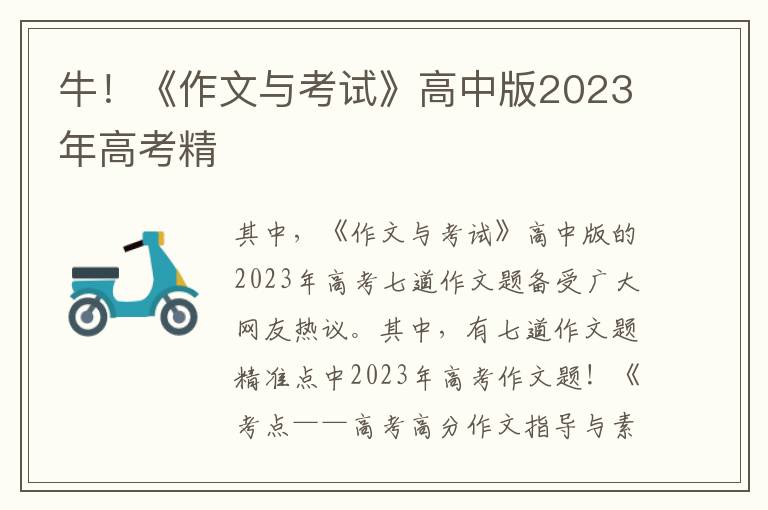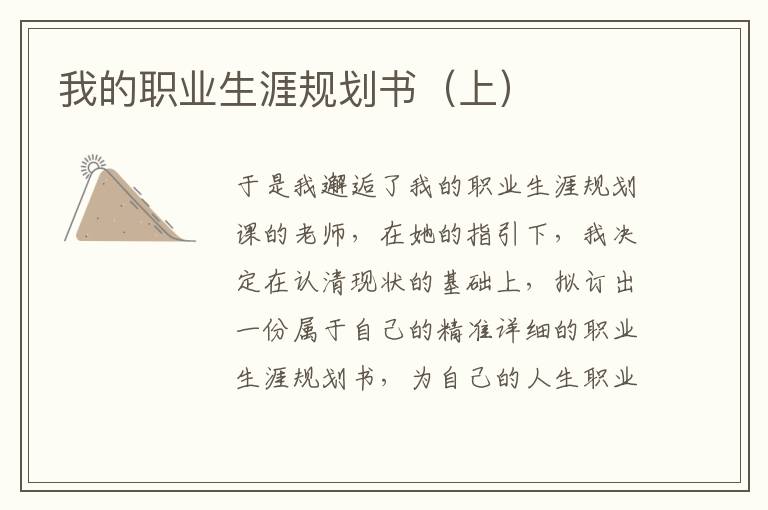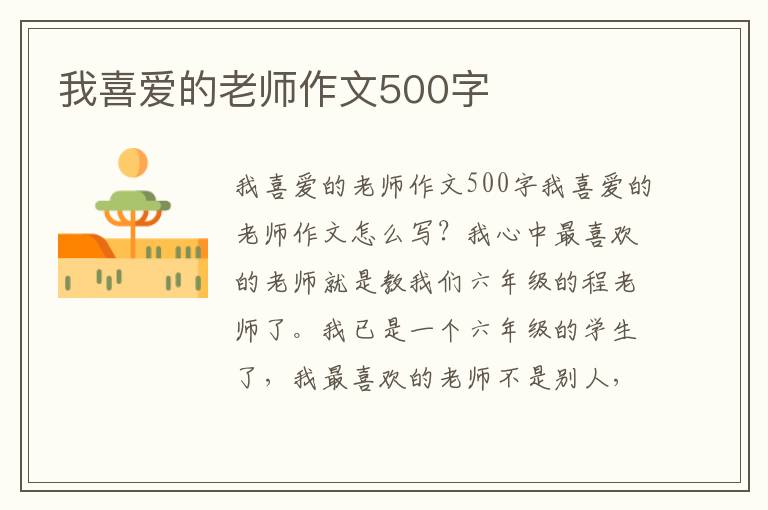老家的熱炕頭抒情散文

老家的熱炕頭抒情散文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總以為,桑拿、汗蒸、瑜伽這些帶有小資情調的消費與我這個勞苦大眾出身的普通人沒有關系,可隨著近年來各種養生保健館的增多,這些昔日的貴族消費項目逐漸走向大眾。這個星期天我就嘗試性地去做了一次汗蒸。換上汗蒸服,躺在焦燙的大炕上,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時候我們老家的土炕。
在我兒時的魯北鄉村,家家戶戶都睡土炕。土炕是用土坯和紅磚盤做的,炕沿用紅磚鑲邊,后來講究一些的也用磁磚鑲邊。呈現在外面的邊緣用紅磚和紅瓦砌出方形和菱形的造型,既為了美觀也為了小孩子上下炕有個蹬腳方便。土炕的絕妙之處在于與隔壁柴屋的灶膛相連接,煙道在土炕中穿越而出,一日三餐生火做飯,就使得土炕熱乎乎的。一方大炕與臥室同寬約4—5米,一家4、5口人睡在一張炕上也不覺得擠。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我一直睡在最貼近灶膛的那一端,那是最熱乎的一段炕頭。炕上鋪上大蘆席,蘆席上鋪著藍印花布做的厚厚的棉花褥子,褥子上面再鋪一層大油布,油布是用來防水防塵的。枕頭是圓柱形的,足有大半米長。印象中炕席子下面總有跳蚤,一掀開褥子,跳蚤就能跳很高。那時的孩子對虱子、跳蚤等小玩意是見多不怪,能抓住就把它放在手心里碾死,抓不住就與它們和諧共處。也有實在忍不住的時候,母親就在炕縫里撒六六粉。據說,這是劇毒農藥,現在都禁用了。但那時好像家家戶戶都用六六粉來除跳蚤。
土炕除了睡覺外,還能在上面吃飯。被子貼著北墻卷起,寬闊的大炕上放下小方桌,一家人圍桌盤腿而坐,小孩子盤不了腿就做小板凳,那種其樂融融的和諧氛圍是現在坐在餐廳的`餐桌上吃飯所沒法比的。吃過晚飯,把筷子和盤碗收拾起,但小桌子不撤。母親還要在上面就著泡子燈納鞋底,孩子們則趴在上面做作業。微弱的燈光下,一家人聚攏在方寸大的小方桌上各行其是。偶爾小孩子打嗝兒放屁就會招來兄妹的奚落和大人的呵斥和數落。
一般9點多鐘小孩子們就打起了哈欠,母親就把小方桌撤下,孩子們各自放下自己的鋪蓋卷,鉆進了溫暖的被窩,先是嘰嘰喳喳地討論一會兒新上映的電影,議論最多的是《小兵張嘎》《地道戰》《鐵道游擊隊》等戰斗片,把鬼子打得滿地找牙,真帶勁。二哥在炕上連蹦帶跳地比劃著能把劉蘭芳的《楊家將》《岳飛傳》等評書復述一遍。睡前的這段時光是輕松歡快的,有時越說越帶勁竟然沒了睡意,母親一遍一遍地催促,“快睡覺吧,明天還要早起上學呢!”把鬧騰的最歡的那個摁下去,慢慢地就都不說話了,一會兒就會聽到此起彼伏的鼾聲。我經常一覺睡醒了,還能看到母親坐在炕頭上為我們做棉衣棉鞋的情形。
土炕上也是全家人勞動的場所。小時候我們村的人靠一項副業打葦簾子創收。蘆葦需要經過切割,剝皮,打磨關節,洗刷,用硫磺熏蒸,最后在架子上用線布袋把一根根蘆葦捆綁在一起,結成葦簾,然后送到收購站賣掉。這是一項很繁瑣的勞動,一般全家老小起上陣。母親用剪刀把蘆葦裁剪出相應的尺寸,哥哥用鐮刀頭打磨葦子關節,姐姐把領來的麻錢整理好纏在小布袋上,我則坐在炕頭上的架子上,上下翻飛線布袋打簾子。葦簾有大小不同的規格,小簾子大約30厘米見方,大簾子是1米57*1。20米;加工一件大簾子能掙1元錢左右,小簾子能掙3角錢。我從7、8歲時就在坐在家里的土炕上打葦簾。十歲以前打小簾子,十歲以后我就開始打大簾子了。把加工好的葦子擺在土炕上,架子放在炕邊,我則挑選粗細均勻的葦子,甩著線布袋一根根編織,我當時個子矮夠不著架子,就在腳底下墊一個小凳子。我打簾子的技術和速度都很嫻熟,記得我上小學時放了學一天就能打完一床大簾子。
那時的時光感覺流淌得很慢,土炕上承載著全家人的生計和活絡,也有孩子們的歡笑和嬉鬧。過去感覺到很辛苦的勞作現在想起來卻也很甜蜜。
時過境遷,時代發展到現在,沒想到在汗蒸房里又享受到了大火炕的溫暖,只是,此時包裝華麗的火炕與彼時的土炕卻大相徑庭,承載的內容和使命也大不相同,過去的土炕承載的是貧瘠生活狀態下的艱辛和全家一起勞作的快樂,現在的汗蒸火炕承載的卻是富裕起來的城市人身體的疲憊焦灼和心靈的孤獨。